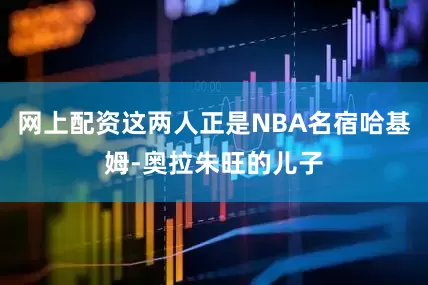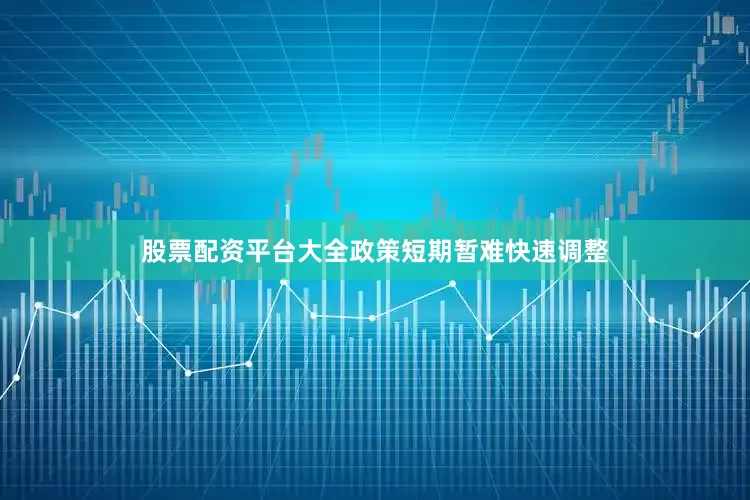#律师来帮忙#
过去,因缺乏平等机会,加上法学学科文化、性别文化及传统任职制度影响,法官职业长期被男性垄断。如今,随着更多女性接受法学教育,法官遴选制度改变,女性有了与男性的同等机会。“学院型”选拔制度下,年轻女法官不断涌现,且在职业中竞争力较强。按此趋势,未来我国女性法官比例或进一步提高,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女性法官人数可能超男性,重塑性别格局。然而,人们潜意识里仍认为法官职业应由男性主导,女性法官处于“他者”地位。当女性法官比例增长“威胁”到男性时,“阴盛阳衰”的言论便开始流传。这反映出人们对女性法官的偏见,而在两性平等的法官职业中,女性法官人数超男性不应被质疑。
尽管男女法官比例失衡的传统格局未彻底改变,但过去几十年法官职业中女性比例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女性法官占比超三分之一且未来仍会增长。大量女性进入法官职业,未来她们的司法权力地位也将提升。在发达城市,女性法官比例不久后可能反超男性,形成“女多男少”局面,与欠发达地区“男多女少”形成反差。建国后前四十年法官职业偏向任用男性,但后来随着法官选任方式改变、预备法官女性居多、离职法官以男性为主,年轻女性法官数量增加、比例提高且年龄结构更年轻。若今后新进法官中女性保持优势,其比例增长会更快,即便在经济落后城市,年轻法官群体中女性比例也在提高且未来会继续上升。
以往法官职业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男性法官数量远高于女性,学者呼吁应给予女性更多进入法官职业的机会。然而,当出现女性法官人数可能激增并超过男性的情况时,有人觉得该转而维护男性法官席位。这种简单逻辑忽略了关键问题:女性在法官职业中的劣势源于诸多“不平等”因素,给予女性更多机会是对“平等”的追求;而女性人数持续增长是“公平竞争”的成果,限制女性进入无疑是再次制造“不平等”。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来讲,过去呼吁任用更多女性法官,是借助“提高女性法官占比”这一手段,达成“消除对女性歧视”的目的,最终实现法官职业的性别平等,并非单纯追求男女法官特定比例。
男女性别比例均等并不等同于实现了法官职业的性别平等。衡量性别平等,需综合级别、收入、社会认可等多重因素,且男女法官数量均等本身并非实现法官职业平等的关键要素。在市场竞争充分、求职者无显著就业偏向时,法官职业需求侧的性别结构应与法学高等教育供给侧的性别结构相近,这才是不考虑性别因素下法官职业合适的男女比例。当下,有人主张控制女性法官数量增长,以防其人数超过男性导致性别比例失衡及负面影响。但这种主张,看似追求平等,实则是排挤女性进入法官职业的借口,并未真正理解法官职业性别平等的内涵,也忽视了合理的性别结构应基于市场与教育等客观状况。
从法律职业理论看,在“三大基石”要求下,法官职业应实现男女平等。专业性是法官职业基本准入门槛,具备丰富法律知识储备与良好司法审判技能是成为法官的主要条件,与性别无关。公共性要求法官职业不能仅体现男性话语权力,还需吸收女性观点意见,若法官职业歧视女性,女性争取权利的声音将难以被听见。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应超越职业身份与性别等因素,建设思维和价值共同体,让男女平等参与,守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自治”目标。因此,职业化发展的法官职业应走“性别中立”路径,即“去性别化”,男女可在充分市场竞争中凭自身努力获得就业和晋升机会,不受性别限制,而非追求男女法官人数均衡。
传统法学学科文化、社会性别塑造及过去任职制度使法官职业长期存在“男多女少”“男强女弱”局面。但近年来,法学院女学生增多,学院型法官选任制度推动法官职业女性比例提高,数量上即将超男性,这并非“问题”,女性法官的性别因素在多数情况下不会给司法决策带来负面影响,反而在一些案件审判中能取得更好效果,且法官职业男女比例应与法学院学生性别比例相当。追求法官职业性别平等不能简单理解为比例均衡而限制女性进入,理想状态是“去性别化”的中性职业,摒弃性别偏见。面对女性法官人数持续增长,未来可在打破职业“天花板”、畅通晋升途径等方面探索研究,真正实现法官职业性别平等。
专业在线股票配资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